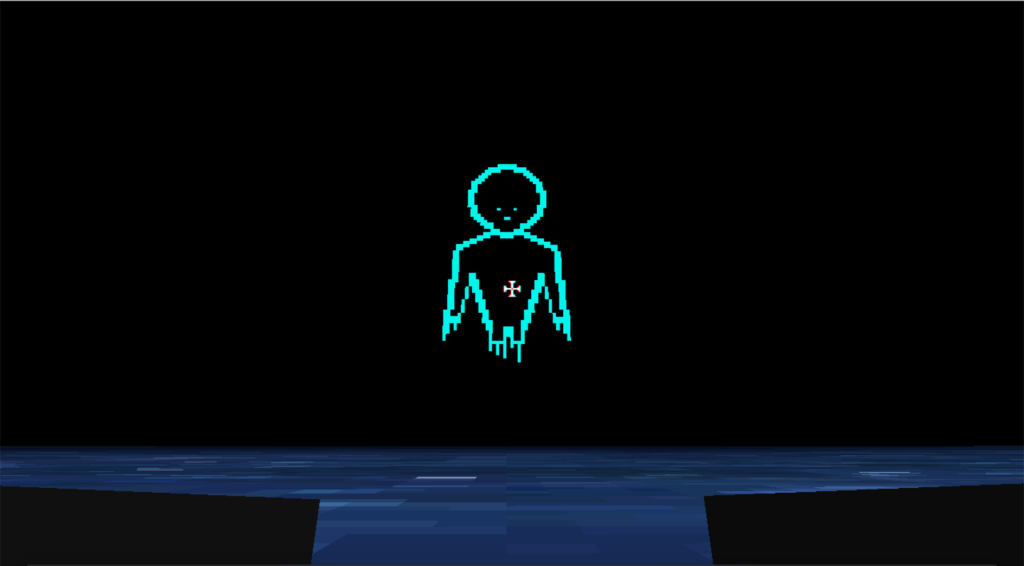椅子在空荡荡的木头盒子里一字排开。开幕,迎接观众的却不是玛莎在契科夫开场的名言,而是人们对特里波列夫戏剧的无意玩笑。饰阿尔卡基娜的Tina Harris演技很不错。她的困惑和愤懑是从腹部迸发的,烦躁是盘根错节于特里波列夫柔嫩心灵的;儿子痛苦而朝气蓬勃的养料使她更显得娇艳欲滴。至于特里波列夫,他冻结在椅子后方,似乎下一秒胸口就要支撑不住地迸出血花一样。然而面对关系密切的母亲,他还是妥协地拥抱她了。
大跌眼镜的是,本能欣赏特里波列夫的医生多尔恩随着Anya Reiss大笔一挥,居然表现得像失去了这一特殊地位:“我喜欢你的剧本……虽然我完全没咋搞懂你想说啥!”可怜的特里波列夫,在契科夫百年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编剧手中还要遭受此等失去知音的酷刑。与此同时,台下绽放出此起彼伏的笑声。这自然也被透明的墙壁阻隔开了。
没有聚光灯的舞台上,观众的目光被全权委托给演员的能动性。除了人为吸引目光的举措外,人物之间巧妙地保持着本质的平等。无论主角还是配角,舞台灯不遗余力地照耀每一人,幸运或不幸的评判在此无足轻重。特里波列夫心中或许有一盏大如车盖的聚光灯悬在头顶,但木头盒子同样认为它毫无意义——毕竟连他的心血、那充斥着晦涩硫磺味的演出内容都被改编家整个删去了,又有谁在乎他的所写所为?
椅子的排列方式逐渐变化,一会背靠着围成圈,一会从靠墙转向前方。玛莎终于抱怨出了她的名言,但自认为不幸的阐述仍是无谓的。就像特里波列夫说:“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那些自以为的艺术祭司坐在缺一面墙、由人工灯光打造的屋子里,就给我们演起人是如何吃、穿的那老一套了!”此时镜头却瞬间切换到缺了一面墙、头顶有人造灯光的全景。我跟右前排的老大叔笑出声。我们的反馈传不到盒子里去,但在嵌套了微型盒子的盒子当中还是足以为人所知的。
妮娜和特里果林在冻结的特里波列夫面前谈及海鸥,一贯公正的人工灯光却倏然曝光似的刺痛了,隔前排的阿姨似乎还打了个寒战。那是一瞬的事,让人怀疑刚才的声响是否是某种清醒梦般的幻觉,但特里波列夫提到“seagull”一词又确实有细微的面部变化,只得暂且将其认为切实的事件。
从始至终,戏剧人物虽然姿态各异,但总归是坐着的。有的望地面,有的望他人,有的看不见视线。特里波列夫是明显的异类:他的背是竖直的,半个体重浮在空中,目光紧追超越木头盒子乃至包裹着盒子的盒子外的某物。他右半身僵硬,一瘸一拐,乃至在其余角色都灵巧地从盒子里下来走向幕后时,观众内心都要不禁发问“跛脚的海鸥哪里下得去场?”
————
开幕,特里波列夫躺在漆黑的盒子中央。背面的墙不见了,“fictional light”也尤其惨白。他席地而坐,其余人则依然有把安坐的椅子。脱离了“平常”与“翻来覆去”这类固有公式的下半场,叙述了数年后数名角色平凡且不幸的人生。
席地而坐的人是特权者,同样意味着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倘若玛莎的黑衣裳是为了给她的生活挂孝,那么特里波列夫的黑衣裳也可以视作他为概念世界而献祭的道袍。悲伤的妮娜与他共享一把椅子的短暂瞬间,也并非主动丢弃现实者回归现实世界的最后机会。一袭黑衣后方是绿色的半塑料椅,椅子只是椅子,没有前后之分。拒绝一把容身位之人,迎接了理想与绝望的死。
————
回家的路上头一次仔细抬头看了看天,原来安娜堡是有星星的,还是头一次知道。
202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