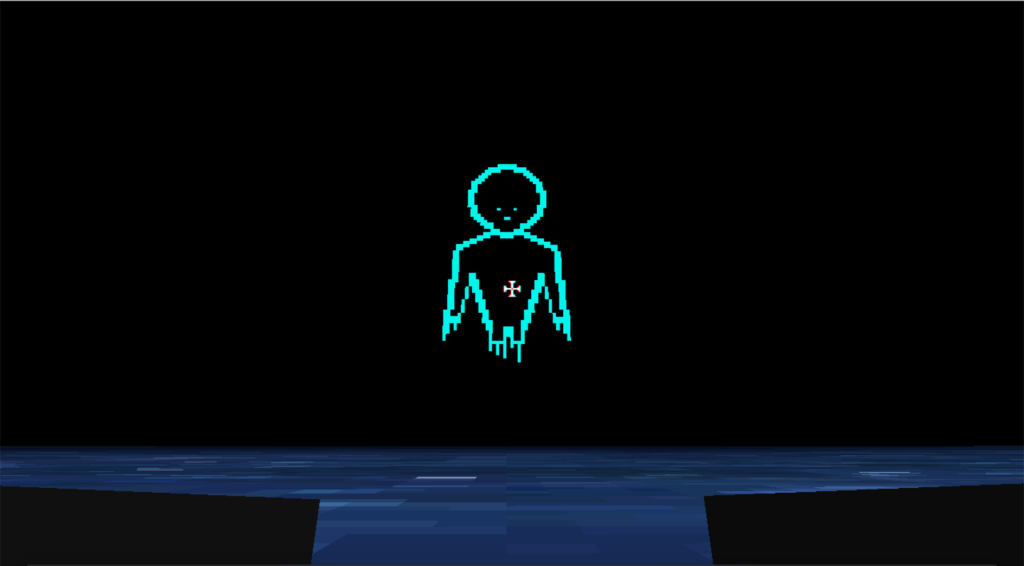校对过程中留下的理解和整合。以前翻校都不留痕,以后应该多养成总结的习惯。
作者:安敏轩 (Nick Admussen),汉学家,诗人,目前于康奈尔大学任亚洲研究系副教授。会议文章发布于2024年5月康奈尔大学的学术工作坊 Pandemic Archives: Media, Geopolitics, and Temporalities of Crisis,标题为 The Postpandemic, the Postsocialist, and Jile Disike (Disco Elysium)。文章将收入安教授与 Shiqi Lin 所编辑的特刊 Pandemic Archives: Media, Geopolitics, and Sociality。
文本引用的是未经审校的版本,由村上侑翻译,并由笔者(无情地)进行了细校。
文章本身是在检视中国玩家对《极乐迪斯科》的反响,并且主张游戏给予的配置与叙事能动性呼应的是一种后社情绪,这种情绪又在(后)疫情时刻重新显现了出来。安教授进而指出这种配置与叙事(而非建构与戏剧)能动性层面的实践,最终会使本应意见相左的群体通过“迪斯科”精神重新融合,形成一种“向未来演进的政治”。
但这里并没有什么华丽的术语,后社会主义就是紧跟着社会主义之后的那段时间,后疫情就是紧跟着疫情结束后的时间。能动性的例子在后面。
不过按笔者理解,很多要点可以概括为:后社会主义带来的情绪与思维方式是“向内”的。
即是说,一方面的缺失必然需求另一方面的补偿。早先的伟大共识崩塌,让人们从外部转而寻求内部(自身),其中也带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风味——例如自我提升,或是急切地想为给自己赋予一个立场/身份1。文中提到改开后的读书热/翻译热/教育热也源于此。
安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认识论崩溃所导致的无力感,以及未来感的缺失。换句话说,外部的稳定消失了,现实又困难重重,人不得不从内部中重新求得一种稳固来抵抗这种无力感。
后社和后疫情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情绪本质是类同的。对宏大叙事和光明未来的信任不复存在,人们只能深入到自我内部去寻找动力。
再来,是要将这种内倾的能动性关联到《极乐迪斯科》上。安教授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提出了能动性的作用。
在游戏设计中,配置-建构能动性(configurative-constructive agency2)互为一组概念,即是指对可控角色“内 vs. 外”的控制权。例如配置能动性可以体现在更改角色技能和属性;建构能动性可以体现在改变游戏场景的地貌和建筑。
另外一组是叙事-戏剧能动性(narrative-dramatic agency),指对于剧情“微观 vs. 宏观”的控制权。例如在对话中选择什么选项,是叙事能动性。你的选择有多大程度影响重要戏剧发展及结局,这是戏剧能动性。
不难看出,配置和叙事能动性是“向内”的那一端,而建构和戏剧能动性则是“向外”的。《极乐迪斯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幅给予了这些“向内”的能动性,而几乎未提供任何“向外”的能动性。哈里(主角)的行动并不改变环境或剧情的走势,而只能在破碎的认知论(或旧有共识)中重塑自我、记忆,重新了解世界。
安教授说到,哈里在开篇的苏醒是一种“深受创伤的系统的重启”。即是说,他颓废且虚无的行为,部分是为了将破碎的既有概念/历史/意识形态拼接在一起,重塑自身的存在和认知。
这种对自我重组的强调,导致一些玩家更看重《极乐迪斯科》中的人物及其关系性,而非作为布景的瑞瓦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化身为瑞瓦肖之声的“天人感应”只是哈里的技能之一,如果完全不予加点,瑞瓦肖产生的作用会十分微弱3。安教授也借此探讨了一些同人创作特征,例如:
- 《极乐迪斯科》的角色可以被放置到另一个IP中
- 人物关系和哈里的人格化心声为主导,布景与(瑞瓦肖的哀伤)氛围可以被替换
- 比起单调的瑞瓦肖建模,粉丝更倾心于游戏奔放的美术风格(例如肖像)
就这样,玩家接纳了这种“向内”的能动性。这是一段在废墟布景中的虚拟旅行,但它同样能为现实生活带来意义,尤其体现在《极乐迪斯科》玩家在“上海极乐迪斯科Only展”抢麦事件与大众截然不同的反应上。
这种类型的能动性似乎塑造了一种“迪斯科”精神——它抛开彰显“向外”能动性的的宏大叙事,而是把视角转向自我塑造与探求,或是对立思想的判断和拼贴。
在游戏中,这和玩家操控哈里所做的事有什么不同呢。
甚至,安教授认为这种向内的“迪斯科”精神也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或原子化,反而这会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团结和政治进程。在飘摇不定的后社/后疫情时刻,人们重新塑造自我、书写历史,怀抱着对未来的描绘前进。
按笔者的理解,这是一个能动性(或者说控制权)由内向外转换的过程4——相当鼓舞人心,但却过于乐观。
诚然,文章所举的上海Only展一度没有预设性别/立场的行为,参会者宽容接纳不确定性与失败,看似其乐融融。但如果脱离了这个爱好和共同点带来的空间,难道玩家们不会退回到自身的身份阵营当中去吗?作者似乎认为“持社会/民族主义立场者”与“BL作者和读者”是差异较大乃至对立的,可是在中国,看似与酷儿接壤的BL作者难道就不会持有民族主义的观念吗?这两拨人在欧美所对应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能像这样直接安放到中国的语境中。
此外,就算《极乐迪斯科》及其精神本身起到了弥合的作用,笔者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亚文化的空间是平行的,一层套着另一层,之间互不侵犯。但当更基础的立场被触动,这个舒适宽容的空间完全有可能破灭,回到以“底线”说话的现实。一轮轮塌房事件足以说明问题,对某个IP近似痴迷的粉丝会因为一点作者的不当言论就迅速割席,不再提及,仿佛之前的热爱都是一场幻梦。在这一层面,《极乐迪斯科》与其它亚文化作品并无本质不同。
此外,在文章中有意义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3月19日(游戏中文本地化发布),但却忽视了Final Cut(发布于2021年3月30日)可能带来的影响。
笔者是于2020年6月26日购得游戏,期间一直持续或间断游玩至2024年9月7日的普通中国玩家。据我有限的观察,在Final Cut发布之前似乎并未有太多关于后社的讨论——这是理所当然的,轻语的简中本地化虽然壮观但并不完美,原文的后社基调也多有遗失。此外,Final Cut发布之前,游戏并不具备包括康米在内的明确阵营线,后社相关的感伤情绪也多限制在文字中。更别说在游戏的早期版本,只有在哈里精神值耗尽后才会浮现如“放弃探案,目标转为建设康米主义”的提示了。
可以说,至少在2020年间,后社的氛围在设计上就相当淡薄。更多人应该是被疫情前就风靡一时的crpg/跑团桌游/洛式恐怖吸引而来。然而,在Final Cut增加了包括康米在内的阵营线,将这一感伤娓娓道来,并且还添加了诸多富有感染力的演出细节后(例如可以通过“见微知著”直接看到曾经屹立在码头,后来却随革命时代一同消失的壮观摩天轮),这种感伤的氛围更加明显了。如若可能,文章可以将Final Cut的发布时间纳入考量,或许会更加呼应“后”疫情的时刻。
总结来说,笔者相当喜欢文章对能动性形式的探讨和关联,尤其是讨论后疫情能动性的部分。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评判,只是笔者不认为这些“向内”的能动性会产生质变、推动未来。事实上,如果文章进一步论述为什么这种能动性就不会造成原子化,与国民的真实生活联系应当会更紧密一些。关于迪斯科精神与酷儿性接壤的部分,由于不熟悉理论框架故暂且保留评价(但此种关联似乎也相当耐人寻味)。
校对亦是一种阅读与联系的过程,能深入阅读海外学者对《极乐迪斯科》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验。包括笔者的意见在内,一些中国社群对未见刊文稿的意见已经返回给作者。在此,笔者要感谢文章的作者安教授,以及翻译了包括本文在内的诸多文献并时常邀请笔者进行校对的侑。祝愿你们热情永驻,新年快乐。